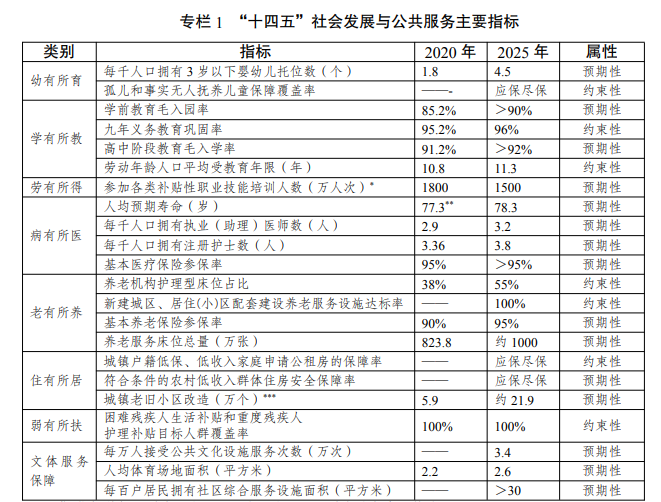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由于网络暴力现象的潜在广度与类别、子类别的多样性,不同国家、文化、学科对网络暴力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确定网络暴力治理工作的重点便成为一个持续的挑战。2022年11月,中央网信办印发规范性文件《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首次规范性明确,“网络暴力针对个人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违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网络秩序。”这种基于网络暴力所侵犯的客体的考量角度,为界定网络暴力概念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在定义网络暴力时可以参照刑法上暴力的概念。
刑法上的暴力是指对人身权利实施的有形或者无形的力量,必须首先作用于个人人身权利。暴力可以被界定为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的明确行为或者象征行为,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和情感暴力等表现形式。据此,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实施的或者在网络中实施的,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的明确行为或者象征行为。
当前常见的网络暴力现象包括网络欺凌、网络诽谤侮辱、网络仇恨言论、网络跟踪、网络恐吓、网络犯罪预告等。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网络空间日趋完善,社会成员在网络空间的参与度、活跃度普遍提高,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并行的“双层社会”构筑起网络时代的特殊社会形态,在为公众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助长了网络暴力向新的表现形式变异。例如产生了谣言诽谤型网络暴力(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谩骂侮辱型网络暴力(寻亲男孩刘某州自杀案)、恶意剪辑型网络暴力(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江无辜女司机被网暴案)、公开隐私型网络暴力(2020年成都确诊女孩被网暴案)、煽动滋事型网络暴力(2020年杨某“性别歧视”被网暴案)等严重破坏网络空间生态的不断翻新的网络暴力表现形式,且网络暴力往往会触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种不法后果。
目前,互联网平台在履行责任、打击网络暴力时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首先,网络暴力的认定标准有待厘清。在内容丰富的互联网中,几乎每天都有争执,但并非每一起事件都能被认定为网络暴力,何种性质的语言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被认定为网暴,如何区分合理的质疑与恶意的网暴。此前,南方都市报曾报道,网暴的判定细则尚待厘清——比如在单个施暴者和数以千百计的施暴者之间、随机偶发和持续不断的网络攻击之间,构成网暴的标准几何,应当考虑网暴评论数量以及在整体评论中的占比情况等等,过度泛化网暴概念可能会造成网暴举目皆是的“视网膜效应”,因此在实践中,需要警惕网暴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其次,人们越来越深度融入网络,但网络中的海量使用者和多样传播方式,意味着平台难以像传统的老师、家长等监护力量那样进行监护,平台也难以有效对于尚未达到网暴标准或尚未造成侵害的极小范围的网络现象进行事先防范与治理。
此外,审核用户发布的信息内容是否属于网络暴力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尤其在现行立法缺失、法律适用模糊的当下,平台仅依靠技术模型进行判定,可能会限缩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现实中平台还会成立专门的信息审核专员团队进行人工校准。然而,人工审核的速度与效率难以与人工智能模型比拟,且不同审核人员的具体判断标准存在差异,难以实现对用户的周延保护。
网络暴力的成因极具复杂性,深受社会伦理及现实、网民心理及情绪等问题影响。可以说,网络暴力是诸多社会问题在网络平台的投射。加之,受能力边界和外部支持程度的限制,平台难以对样本库以外的涉网暴信息进行有效识别并切断传播。网暴具有线上线下跳转或蔓延的特点,平台只能对网络内容与账号进行管理,无法对现实中的网民个人产生直接影响。
事实上,预防和治理网络暴力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的庞大课题,除了平台方需要倾注努力,还需监管部门、用户、媒体等多方主体的协作支持、共同参与。其中,监管部门应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和细则制定,首先明确网络暴力判断标准,为平台落实网络暴力的管理责任提供指导,也为用户审视、约束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言行提供依据。此外,还需确保网络暴力治理执法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对于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网络暴力行为施以妥善处罚,以实现有效威慑与制裁。对于媒体而言,应主动尽到事实核查责任,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相关事件进行报道,避免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加剧网络暴力恶性事件的发酵与传播。在一场网络暴力事件中,用户可能是直接施暴者、直接或间接传播者,也可能是受害者。用户应注重规范自身“文明上网”的行为习惯,严守言论自由的义务边界,提高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识别能力,及时举报相关内容,学习了解有关平台防范网络暴力的功能机制,做好自我防护,避免网络暴力再次发生。(作者:郭旨龙-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副教授,郭斯文-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同心县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III级/较重] 【2023-05-30】](http://img.yazhou.964.cn/2022/0610/202206101026473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