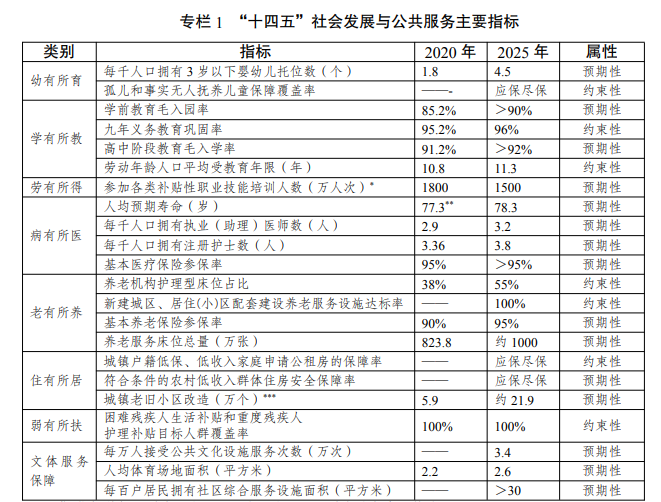邹艳艳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故乡的模样。
故乡看似平凡,却宽和地疗愈和滋养着每一个路过的人们。我也有过这样一片故土,身在其中时浑然不觉,离开多年后却深深怀念。
 (资料图)
(资料图)
我出生在湖北枣阳,6岁随家人迁居至南疆的一个部队农场。儿时的记忆早已模糊,我们都固执地认为湖北是父母怀念的故乡,而我们喧哗肆意地生活过的恰斯农场才是属于我们孩子的故乡。恰斯农场是一个棉花种植基地,远离县城,交通闭塞,毗邻叶尔羌河。
不知是因为对故乡的偏爱还是对逝去时光一去不返的追忆,故乡似已在记忆里被悄然镀上金边。总觉得,此生看过的最洁澈的云朵、最繁亮的星星、最温柔的垂柳都是在恰斯农场。孩童时,父母忙于农活生计,孩子们却也乐得无所束缚,总是有大把的时间去探索世界。
我经常观察云朵的变换,并惊异于蓝天与白云可以相配得如此浑然天成。也在夏夜里躺在凉席上数星星找星座,彼时繁星如毯,铺天而盖,美得让人此生难忘。即便是性格喜静的我,也在这里收获了一段足够喧哗快乐的时光,在雨后的草丛里寻找新发的蘑菇,在浇过水的棉田里堵道网鱼,在放学路上摘吃桑葚沙枣,在田埂上挖苜蓿辨野草。
离开故乡后,我时常怀念恰斯农场那虽以萧瑟为底色,却由多种颜色汇成的分明四季。在那里,可以慢慢品味冬日的树木萧索、寒风凛冽、白雪皑皑,春日里大地苏醒后的嫩芽新发、野花摇曳和沙尘滚滚,夏日里随处可见绿油油的棉田、芦苇和烈日暴晒的戈壁滩,秋日树叶由绿逐渐枯萎变黄、飘落一地,连绵棉田被覆盖上灿烂的白色或彩色棉朵。因为灌溉需要,恰斯农场的每一条路几乎都连着浇水的渠道,道路两旁种满了白杨树、沙枣树、桑葚树和垂柳。孩子们在水渠里捉鱼、洗澡、溜冰,大人们则在炎炎夏日躲在垂柳下乘凉洗衣。
小时候,我很喜欢坐在姥爷床边听他抽着烟斗讲故事,也常常觊觎他那个破旧的书箱。每每得到一本书,他看完后总会马上传给我读,这已然成为我们的默契。姥爷在村里有个好友会说书,人们总喜欢在夜里围坐在凉席上听他讲《倚天屠龙记》。每次结束他都会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人们带着遗憾的嘘声散去,度过了一个个美好而普通的夏夜。
每一个在恰斯农场长大的孩子,和恰斯部队都有着不浅的缘分。童年里,我们熟悉拉练和跑操声,常见一片迷彩绿,也爱过军营民谣,《解放军报》更是我童年的启蒙读物之一。犹记得,我初到恰斯农场上学时,学校条件非常恶劣,两排老旧平房外加一片盐碱地操场就是全部的教学场地。教室里墙壁裂缝,一到泛碱季节地下就冒积水,阴冷潮湿,学生们只能在脚下垫两块砖头上课。
后来,军区领导组织官兵募捐,选址修建了我的母校——恰斯希望学校。这所学校的建成在当时颇为轰动,崭新的两层小楼成为当地最好的建筑,白亮的瓷砖上镌刻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为学校募捐的官兵,但每一个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生都会深深感激他们。教育足以改变每个孩子的命运轨迹,也改变了我。在这栋教学楼里,虽然师资匮乏,学习资料奇缺,但是小学和初中生涯却是格外单纯快乐,同学之间喧哗打闹、相约上学、偷抄作业、互赠明信片。后来,我们那一届成为建校后第一批考入喀什地区重点高中的学生。其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如当年的我们一样从这栋二层小楼走向大江南北,展开全新的人生。
离开喀什多年,那里对我来说,不仅是有着沙漠、胡杨、巴扎、囊馍的旅游之所,更是我爱过的故乡。回望故乡,除了深深的怀念,更多的是感激,感谢那片曾经见证我许多欢乐忧伤的土地,感激那段岁月里所有爱过我我也爱过的人们,包括温柔的杨柳、连绵的棉田,我都记得你们。
远隔万里之外,遥祝故乡更好。谢谢你曾是我们的乐土和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